译文及注释
赏析
猜您喜欢
赋妇人染红指甲
凤华香染水晶寒,碎系珊瑚玉笋间,想别离拄齿应长叹。污檀脂数点斑,记归期刻损朱阑。锦瑟弦重按,杨家花未残,为何人血泪偷弹?
柔荑春笋蘸丹砂,腻骨凝脂贴绛纱,多应泣血淹罗帕。洒筼筜赪素甲,抹胭脂误染冰楂。横象管跳红玉,理筝弦点落花,轻掐碎残霞。
丹枫软玉笋梢扶,猩血春葱指上涂,偷研点易朱砂露。蘸冰痕书绛符,摘蟾宫丹桂扶疏。潮醉甲霞生晕,碾秋磦琼素举,夹竹桃香符。
凤华香染水晶寒,碎系珊瑚玉笋间,想别离拄齿应长叹。污檀脂数点斑,记归期刻损朱阑。锦瑟弦重按,杨家花未残,为何人血泪偷弹?
柔荑春笋蘸丹砂,腻骨凝脂贴绛纱,多应泣血淹罗帕。洒筼筜赪素甲,抹胭脂误染冰楂。横象管跳红玉,理筝弦点落花,轻掐碎残霞。
丹枫软玉笋梢扶,猩血春葱指上涂,偷研点易朱砂露。蘸冰痕书绛符,摘蟾宫丹桂扶疏。潮醉甲霞生晕,碾秋磦琼素举,夹竹桃香符。
重阳来未。谁领黄花意。斟玉醑,歌金缕。云山笼瑞彩,风月熔清气。北山顶,寿星一点光无际。
六十今朝是。甲子从头起。堂堂去,千千岁。是非华表鹤,深浅蓬莱水。翁不管,年年先共黄花醉。
六十今朝是。甲子从头起。堂堂去,千千岁。是非华表鹤,深浅蓬莱水。翁不管,年年先共黄花醉。
君恩九鼎重,臣命一毫轻。出身事主,刚甚须作不平鸣。老却西山薇蕨,闲损南窗松菊,羞死汉公卿。豺狼敢横道,草木要知名。
秋已素,人又去,若为情。长沙何在,风送呜咽暮潮声。举棹却寻归路,挥尘莫谈时事,得酒且频倾。一片古时月,千里伴君行。
秋已素,人又去,若为情。长沙何在,风送呜咽暮潮声。举棹却寻归路,挥尘莫谈时事,得酒且频倾。一片古时月,千里伴君行。
 今释
今释 白居易
白居易 刘向
刘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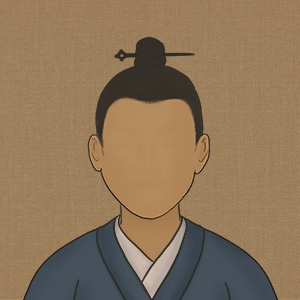 周文质
周文质 王建
王建 叶梦得
叶梦得 高鹗
高鹗 辛弃疾
辛弃疾 张抡
张抡 石孝友
石孝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