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普(公元一二四四年至一三一五年)生于宋理宗淳祐四年,卒于元仁宗延祐二年,年七十二岁。居石堂山。入元,隐居教授,从学者数百人。三辟为本省教授,不起。当聘主云庄书院。晚居莆中,造就益众。普著述有石堂遗稿四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猜您喜欢
第一折
(冲末扮周舍上,诗云)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自家郑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儿周舍是也。自小上花台做子弟。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引章。他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娶他,争奈他妈儿不肯。我今做买卖回来。今日特到他家去,一来去望妈儿,二来就提这门亲事,多少是好。(下)(卜儿同外旦上,云)老身汴梁人氏,自身姓李。夫主姓宋,早年亡化已过。止有这个女孩儿,叫做宋引章。俺孩儿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般不晓,无般不会。有郑州周舍,与孩儿作伴多年。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只是老身谎彻梢虚,怎么便肯?引章,那周舍亲事,不是我百般板障,只怕你久后自家受苦。(外旦云)奶奶,不妨事,我一心则待要嫁他。(卜儿云)随你,随你!(周舍上,云)咱家周舍,来此正是他门首,只索进去。(做见科)(外旦云)周舍,你来了也!(周舍云)我一径的来问亲事,母亲如何?(外旦云)母亲许了亲事也。(周舍云)我见母亲去。(做见卜儿科)(周舍云)母亲,我一径的来问这亲事哩。(卜儿云)今日好日辰,我许了你,则休欺负俺孩儿。(周舍云)我并不敢欺负大姐。母亲,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请下者,我便收拾来也。(卜儿云)大姐,你在家执料,我去请那一辈儿老姊妹去来。(周舍诗云)数载间费尽精神,到今朝才许成亲。(外旦云)这都是天缘注定,(卜儿云)也还有不测风云。(同下)(外扮安秀实上,诗云)刘蕡下第千年恨,范丹守志一生贫。料得苍天如有意,断然不负读书人。小生姓安名秀实,洛阳人氏。自幼颇习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到此汴梁,有一歌者宋引章和小生作伴。当初他要嫁我来,如今却嫁了周舍。他有个八拜交的姐姐是赵盼儿,我去央他劝一劝,有何不可。赵大姐在家么?(正旦扮赵盼儿上,云)妾身赵盼儿是也。听的有人叫门,我开门看咱。(见科,云)我道是谁,原来是妹夫。你那里来?(安秀实云)我一径的来相烦你。当初姨姨要引章嫁我来,如今却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劝他一劝。(正旦云)当初这亲事不许你来?如今又要嫁别人,端的姻缘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妓女追陪,觅钱一世,临收计,怎做的百纵千随,知重咱风流媚。
【混江龙】我想这姻缘匹配,少一时一刻强难为。如何可意?怎的相知?怕不便脚搭着脑杓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后迟!寻前程,觅下梢,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料的来人心不问,天理难欺。
【油葫芦】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遮莫向狗溺处藏,遮莫向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
【天下乐】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
(云)妹夫,我可也待嫁个客人。有个比喻。(安秀实云)喻将何比?(正旦唱)
【那吒令】待妆个老实,学三从四德;争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端的是那里是三梢末尾?俺虽居在柳陌中、花街内,可是那件儿便宜?
【鹊踏枝】俺不是卖查梨,他可也逞刀锥;一个个败坏人伦,乔做胡为。(云)但来两三遭,问那厮要钱,他便道:"这弟子敲馒儿哩!"(唱)但见俺有些儿不伶俐,便说是女娘家要哄骗东西。
【寄生草】他每有人爱为娼妓,有人爱作次妻。干家的干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计。他正是"南头做了北头开,东行不见西行例"。
(云)妹夫,你且坐一坐,我去劝他。劝的省时,你休欢喜;劝不省时,休烦恼。(安秀实云)我不坐了,且回家去等信罢。大姐留心者!(下)(正旦做行科,见外旦云)妹子,你那里人情去?(外旦云)我不人情去,我待嫁人哩!(正旦云)我正来与你保亲。(外旦云)你保谁?(正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谁?(外旦云)我嫁周舍。(正旦云)你如今嫁人,莫不还早哩?(外旦云)有甚么早不早!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儿脓。我嫁了,做一个张郎家妇,李郎家妻,立个妇名,我做鬼也风流的。(正旦唱)
【村里迓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纪小哩,我与你慢慢的别寻个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铜斗儿家缘家计。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肠话劝妹妹,我怕你受不过男儿气息。
(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不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外旦云)你说我听咱。(正旦唱)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他终不解其意;那做子弟的,他影儿里会虚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实。(外旦云)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也堪爱哩。(正旦唱)那厮虽穿着几件虼螂皮,人伦事晓得甚的!
(云)妹子,你为甚么就要嫁他?(外旦云)则为他知重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他怎么知重你?(外旦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铺盖儿暖了,着你妹子歇息。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鐶。只为他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正旦云)你原来为这般呵。(唱)
【上马娇】我听的说就里,你原来为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冬月间着炭火煨,烘炙着绵衣。
【游四门】吃饭处,把匙头挑了筋共皮;出门去,提领系,整衣袂,戴插头面整梳篦。衜一味是虚脾,女娘每不省越着迷。
【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
【幺篇】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准?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云)妹子,久以后你受苦呵,休来告我。(外旦云)我便有那该死的罪,我也不来央告你。(周舍上,云)小的每,把这礼物摆的好看些。(正旦云)来的敢是周舍?那厮不言语便罢,他若但言,着他吃我几嘴好的。(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请姨姨吃些茶饭波。(正旦云)你请我?家里饿皮脸也,揭了锅儿底?窨子里秋月--不曾见这等食?(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门亲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谁?(周舍云)保宋引章。(正旦云)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儿?保他那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生儿长女?(周舍云)这歪刺骨好歹嘴也!我已成了事,不索央你。(正旦云)我去罢。(做出门科)(安秀实上,云)姨姨,劝的引章如何?(正旦云)不济事了也。(安秀实云)这等呵,我上朝求官应举去罢。(正旦云)你且休去,我有用你处哩。(安秀实云)依着姨姨说,我且在客店中安下,看你怎么发付我。(下)(正旦唱)
【赚煞】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缠郎君天魔祟。则他那裤儿里休猜做有腿,吐下鲜红血则当做苏木水。耳边休采那等闲食,那的是最容易、剜眼睛嫌的,则除是亲近着他便欢喜。(带云)着他疾省呵!(唱)哎,你个双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带云)一个夫人来到手儿里了。(唱)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下)
(周舍云)辞了母亲,着大姐上轿,回咱郑州去来。(诗云)才出娼家门,便作良家妇。(外旦诗云)只怕吃了良家亏,还想娼家做。(同下)
第二折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骑马一世,驴背上失了一脚。我为娶这妇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头,才成得事。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我骑了马,离了汴京,来到郑州。让他轿子在头里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话。则见那轿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抬轿的小厮,道:"你这等欺我!"举起鞭子就打。问他道:"你走便走,晃怎么?"那小厮道:"不干我事,奶奶在里边不知做甚么?"我揭起轿帘一看,则见他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来到家中,我说:"你套一床被我盖。"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那里?"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甚么?"他道:"我套绵子,把我翻在里头了。"我拿起棍来,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外旦云)我那里有这等事?(周舍云)我也说不得这许多。兀那贱人,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来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云)不信好人言,必有忄西惶事。当初赵家姐姐劝我不听,果然进的门来,打了我五十杀威棒。朝打暮骂,怕不死在他手里?我这隔壁有个王货郎,他如今去汴梁做买卖。我写一封书捎将去,着俺母亲和赵家姐姐来救我。若来迟了,我无那活的人也。天那,只被你打杀我也!(下)(卜儿哭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亲便是。有我女孩儿,从嫁了周舍,昨日王货邮寄信来,上写着道:"从到他家,进门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赵家姐姐来救我。"我拿着书,去与赵家姐姐说知,怎生救他去。引章孩儿,则被你痛杀我也!(下)(正旦上,云)自家赵盼儿。我想这门衣饭,几时是了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听的道谁揭债、谁买休。他每待强巴结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楼?一个个眼张狂。似漏了网的游鱼,一个个嘴卢都似跌了弹的斑鸠。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他每初时间有些实意,临老也没回头。
【逍遥乐】那一个不因循成就,那一个不顷刻前程,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和爷娘结下不厮见的冤仇,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儿机彀。他使那千般贞烈,万种恩情,到如今一笔都勾。
(卜儿上,云)这是他门首,我索过去。(做见科,云)大姐,烦恼杀我也。(正旦云)奶奶,你为甚么这般啼哭?(卜儿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听你劝,嫁了周舍,进门去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姐姐,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打了也!(唱)
【金菊香】想当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当初作念你的言词,今日都应口。则你那去时,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幸的班头,还说道有恩爱、结绸缪。
【醋葫芦】你铺排着鸳衾和凤帱,指望效天长共地久。蓦入门,知滋味,便合体。几番家眼睁睁打干净,待离了我这手。(带云)赵盼儿,(唱)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云)既然是这般呵,谁着你嫁他来?(卜儿云)大姐,周舍说誓来。(正唱)
【幺篇】那一个不嘇可可道横死亡?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则你这亚仙子母老实头。普天下爱女娘的子弟口,(带云)奶奶,不则周舍说慌也。(唱)那一个不指皇天各般说咒?恰似秋风过耳早休休。(卜儿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儿?(正旦云)奶奶,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卜儿云)他说来:"则有打死的,无有买休卖休的。"(正旦寻思科,做与卜耳语科,云)……则除是这般。(卜儿云)可是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将书来我看。(卜递书科,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奶奶:当初不信好人之言,果有忄西惶之事。进得他门,便打我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你来的早,还得见我;来得迟呵。不能勾见我面了。只此拜上。"妹子也,当初谁教你做这事来!(唱)
【幺篇】想当初有忧呵同共忧,有愁呵一处愁。他道是残生早晚丧荒丘,做了个游街野巷村务酒。你道是百年之后,(云)妹子也,你不道来:"这个也大姐,那个也大姐,出了一包脓!不如嫁个张郎妇、李郎妻,(唱)立一个妇名儿,做鬼也风流!"(云)奶奶,那寄书的人去了不曾?(卜儿云)还不曾去哩。(正旦云)我写一封书,寄与引章去。(做写科,唱)
【后庭花】我将这知心书亲自修,教他把天机休泄漏。传示与休莽戆收心的女,拜上你浑身疼的歹事头。(带云)引章,我怎的劝你来。(唱)你好没来由,遭他毒手,无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鲜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将性命丢!况家乡隔郑州,有谁人相睬瞅,空这般出尽丑。
(卜儿哭科,云)我那女孩儿那里打熬得过!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奶奶,放心!(唱)
【柳叶儿】则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个机谋。把这云鬟蝉鬓妆梳就,(带云)还再穿上些锦绣衣服。(唱)珊瑚钩、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儿别样娇柔。
【双雁儿】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割舍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个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说大口,怎出得我这烟月手!
(卜儿云)姐姐,到那里仔细着。(哭科,云)孩儿,则被你烦恼杀了我也!(正旦唱)
【浪里来煞】你收拾了心上忧,你展放了眉间皱,我直着"花叶不损觅归秋"。那厮爱女娘的心,见的便似驴共狗,卖弄他玲珑剔透。(云)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俱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撤了。我这里出了门儿,(唱)可不是一场风月,我着那汉一时休。(下)
第三折
(周舍同店小二上,诗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无非花共酒,恼乱我心肠。店小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我那里稀罕你那房钱养家?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头乱,一时间那里寻你去?(周舍云)你来粉房里寻我。(小二云)粉房里没有呵?(周舍云)赌房里来寻。(小二云)赌房里没有呵?(周舍云)牢房里来寻。(下)(丑扮小闲,挑笼上,诗云)钉靴雨伞为活计,偷寒送暖作营生。不是闲人闲不得,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自家张小闲的便是。平生做不的买卖,止是与歌者姐姐每叫些人,两头往来,传消寄信都是我。这里有个大姐赵盼儿,着我收拾两箱子衣服行李,往郑州去。都收拾停当了。请姐姐上马。(正旦上,云)小闲,我这等打扮,可冲动得那厮么?(小闲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么哩?(小闲云)休道冲动那厮,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则为他满怀愁,心间闷,做的个进退无门。那婆娘家一涌性,无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
【滚绣球】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输个姓因,怎不教那厮背槽抛粪!更做道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献勤,几番家待要不问;第一来我则是可怜见无主娘亲,第二来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到那里呵,也索费些精神。
(云)说话之间,早来到郑州地方了。小闲,接了马者,且在柳阴下歇一歇咱。(小闲云)我知道。(正旦云)小闲,咱闲口论闲话:这好人家好举止,恶人家恶家法。(小闲云)姐姐,你说我听。(正旦唱)
【倘秀才】县君的则是县君,妓人的则是妓人。怕不扭捏着身子蓦入他门;怎禁他使数的到支分,背地里暗忍。
【滚绣球】那好人家将粉扑儿浅淡匀,那里像咱干茨腊手抢着粉;好人家将那篦梳儿慢慢地铺鬓,那里像咱解了那襻胸带,下劾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个远近,觑个向顺,衜一味良人家风韵;那里像咱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个猢孙。有那千般不实乔躯老,有万种虚嚣歹议论,断不了风尘。
(小闲云)这里一个客店,姐姐好住下罢。(正旦云)叫店家来。(店小二见科)(正旦云)小二哥,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儿,放下行李。你与我请将周舍来,说我在这里久等多时也。(小二云)我知道。(做行叫科,云)小哥在那里?(周舍上,云)店小二,有甚么事?(小二云)店里有个好女子请你哩。(周舍云)咱和你就去来。(做见科,云)是好一个科子也。(正旦云)周舍,做来了也。(唱)
【幺篇】俺那妹子儿有见闻,可有福分,抬举的个丈夫俊上添俊,年纪儿恰正青春。(周舍云)我那里曾见你来?我在客伙里,你弹着一架筝,我不与了你个褐色绸缎儿?(正旦云)小的,你可见来?(小闲云)不曾见他有甚么褐色绸缎儿。(周舍云)哦,早起杭州客伙散了,赶到陕西客伙里吃酒,我不与了大姐一分饭来?(正旦云)小的每,你可见来?(小闲云)我不曾见。(正旦唱)你则是忒现新,忒忘昏,更做道你眼钝。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我为你断梦劳魂。(周舍云)我想起来了,你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你是赵盼儿,好,好!当初破亲也是你来!小二,关了店门,则打这小闲。(小闲云)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一房一卧来嫁你,你倒打我?(正旦云)周舍,你坐下,你听我说。你在南京时,人说你周舍名字,说的我耳满鼻满的,则是不曾见你。后得见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饭,只是思想着你。听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恼?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亲!(唱)
【倘秀才】我当初倚大呵妆儇主婚?怎知我嫉妒呵特故里破亲?你这厮外相儿通疏就里村!你今日结婚姻,咱就肯罢论。
(云)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奁房来寻你,你刬地将我打骂。小闲,拦回车儿,咱家去来!(周舍云)早知姐姐来嫁我,我怎肯打舅舅?(正旦云)你真个不知道?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门,只守着我坐下。(周舍云)休说一两日,就是一两年,您儿也坐的将去。(外旦上,云)周舍两三日不家去,我寻到这店门首。我试看咱,原来是赵盼儿和周舍坐哩!兀那老弟子不识羞,直赶到这里来!周舍,你再不要来家,等你来时,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递一刀子戳哩。(下)(周舍取棍科,云)我和你抢生吃哩!不是奶奶在这里,我打杀你!(正旦唱)
【脱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饶人,我为甚不敢明闻;肋底下插柴自忍,怎见你便打他一顿?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时节背地里使些村,对着我合思忖:那一个双同叔打杀俏红裙?
【幺篇】则见他恶哏哏,摸按着无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云)你拿着偌粗的棍棒,倘或打杀他呵,可怎了?(周舍云)丈夫打杀老婆,不该偿命。(正旦云)这等说,谁敢嫁你?(背唱)我假意儿瞒,虚科儿喷,着这厮有家难奔。妹子也。你试看咱风月救风尘。
(云)周舍,你好道儿!你这里坐着,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小闲,拦回车儿,咱回去来!(周舍云)好奶奶,请坐!我不知道他来;我若知道他来,我就该死。(正旦云)你真个不曾使他来?这妮子不贤惠,打一棒快球子。你舍的宋引章,我一发嫁你。(周舍云)我到家里就休了他。(背云)且慢着,那个妇人是我平日间打怕的,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休的造次,把这婆娘摇撼的实着。(向旦云)奶奶,您孩儿肚肠是驴马的见识,我今家去把媳妇休了呵,奶奶,你把肉吊窗儿放下来,可不嫁我,做的个尖担两头脱。奶奶,你说下个誓着。(正旦云)周舍,你真个要我赌咒?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的我赌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将酒来。(正旦云)休买酒,我车儿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还要买羊。(正旦云)休买羊,我车上有个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我买红去。(正旦云)休买红,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周舍,你争甚么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唱)
【二煞】则这紧的到头终是紧,亲的原来只是亲。凭着我花朵儿身躯、笋条几年纪,为这锦片儿前程,倒赔了几锭儿花银。拚着个十米九糠,问甚么两妇三妻,受了些万苦千辛。我着人头上气忍,不枉了一世做郎君。
【黄钟尾】你穷杀呵,甘心守分捱贫困;你富呵,休笑我饱暖生淫惹议论。您心中觑个意顺。但休了你这门内人,不要你钱财使半文。早是我走将来自上门。家业家私待你六亲,肥马轻裘待你一身,倒贴了奁房和你为眷姻。(云)我若还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都不晓得一些儿的。(唱)我将你写了的休书正了本。(同下)
第四折
(外旦上,云)这些时周舍敢待来也?(周舍上,见科)(外旦云)周舍,你要吃甚么茶饭?(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将纸笔来,写与你一纸休书,你快走!(外旦接休书不走科,云)我有甚么不是,你休了我?(周舍云)你还在这里?你快走!(外旦云)你真个休了我?你当初要我时怎么样说来?你这负心汉,害天灾的!你要去,我偏不去。(周舍推出门科)(外旦云)我出的这门来。周舍,你好痴也!赵盼儿姐姐,你好强也。我将着这休书,直至店中寻姐姐去来。(下)(周舍云)这贱人去了,我到店中娶那妇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恰才来的那妇人在那里?(小二云)你刚出门,他也上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儿了!将马来,我赶将他去。(小二云)马揣驹了。(周舍云)鞴骡子。(小二云)骡子漏蹄。(周舍云)这等,我步行赶将他去。(小二云)我也赶他去。(同下)(旦同外旦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勾出的这门也!(正旦云)走、走、走!(唱)
【双调】【新水令】笑吟吟案板似写着休书,则俺这脱空的故人何处?卖弄他能爱女、有权术,怎禁那得胜葫芦说到有九千句。
(云)引章,你将那休书来与我看咱。(外旦付休书)(正旦换科,云)引章,你再要嫁人时,全凭这一张纸是个照证,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赶上,喝云)贱人,那里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周舍,你与了我休书,赶出我来了。(周舍云)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外旦展看,周夺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碎我的休书也。(旦上救科)(周舍云)你也是我的老婆(正旦云)我怎么是你的老婆?(周舍云)你吃了我的酒来。(正旦云)我车上有十瓶好酒,怎么是你的,(周舍云)你可受我的羊来。(正旦云)我自有一只熟羊,怎么是你的?(周舍云)你受我的红定来。(正旦云)我自有大红罗,怎么是你的?(唱)
【乔牌儿】酒和羊,车上物;大红罗,自将去。你一心淫滥无是处,要将人白赖取。
(周舍云)你曾说过誓嫁我来。(正旦唱)
【庆东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
(云)引章妹子,你跟将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正旦唱)
【落梅风】则为你思虑,忒模糊。(周舍云)休书已毁了,你不跟我去待怎么?(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子休慌莫伯!咬碎的是假休书。(唱)我特故抄与你个休书
题目,我跟前见放着这亲模。(周舍夺科)(正旦唱)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周扯二旦科,云)明有王法,我和你告官去来。(同下)(外扮孤引张千上,诗云)声名德化九重闻,良夜家家不闭门。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小官郑州守李公弼是也。今日升起早衙,断理些公事。张千,喝撺箱。(张千云)理会的。(周舍同二旦、卜儿上)(周叫云)冤屈也!(孤云)告甚么事?(周舍云)大人可怜见,混赖我媳妇。(孤云)谁混赖你的媳妇?(周舍云)是赵盼儿设计混赖我媳妇宋引章。(孤云)那妇人怎么说?(正旦云)宋引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强占为妻,昨日又与了休书,怎么是小妇人混赖他的!(唱)
【雁儿落】这厮心狠毒,这厮家豪富,衜一味虚肚肠,不踏着实途路。
【得胜令】宋引章有亲夫,他强占作家属。淫乱心情歹,凶顽胆气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现放着体书,望恩官明鉴取。
(安秀实上,云)适才赵盼儿使人来说;"宋引章已有休书了,你快告官去,便好娶他。"这里是衙门首,不免高叫道:冤屈也!(孤云)衙门外谁闹?拿过来!(张千拿入科,云)告人当面。(孤云)你告谁来?(安秀实云)我安务实,聘下宋引章,被郑州周舍强夺为妻,乞大人做主咱!(孤云)谁是保亲?(安秀实云)是赵盼儿。(孤云)赵盼儿,你说宋引章原有丈夫,是谁?(正旦云)正是这安秀才。(唱)
【沽美酒】他幼年间便习儒,腹隐着九经书;又是俺共里同村一处居,接受了钗环财物,明是个良人妇。
(孤云)赵盼儿,我问你。这保亲的委是你么?(正旦云)是小妇人。(唱)
【太平令】现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怎当他抢亲的百计亏图?那里是明婚正娶,公然的伤风败俗!今日个诉与太府做主,可怜见断他夫妻完聚。(孤云)周舍,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你怎生还赖是你的妻子?若不看你父亲面上,送你有司问罪!您一行人,听我下断:周舍杖六十,与民一体当差。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赵盼儿等宁家住坐。(词云)只为老虔婆爱贿贪钱,赵盼儿细说根源。呆周舍不安本业,安秀才夫妇团圆。(众叩谢科)(正旦唱)
【收尾】对恩官一一说缘故,分剖开贪夫怨女。面糊盆再休说死生交,风月所重谐燕莺侣。
题目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正名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冲末扮周舍上,诗云)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自家郑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儿周舍是也。自小上花台做子弟。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引章。他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娶他,争奈他妈儿不肯。我今做买卖回来。今日特到他家去,一来去望妈儿,二来就提这门亲事,多少是好。(下)(卜儿同外旦上,云)老身汴梁人氏,自身姓李。夫主姓宋,早年亡化已过。止有这个女孩儿,叫做宋引章。俺孩儿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般不晓,无般不会。有郑州周舍,与孩儿作伴多年。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只是老身谎彻梢虚,怎么便肯?引章,那周舍亲事,不是我百般板障,只怕你久后自家受苦。(外旦云)奶奶,不妨事,我一心则待要嫁他。(卜儿云)随你,随你!(周舍上,云)咱家周舍,来此正是他门首,只索进去。(做见科)(外旦云)周舍,你来了也!(周舍云)我一径的来问亲事,母亲如何?(外旦云)母亲许了亲事也。(周舍云)我见母亲去。(做见卜儿科)(周舍云)母亲,我一径的来问这亲事哩。(卜儿云)今日好日辰,我许了你,则休欺负俺孩儿。(周舍云)我并不敢欺负大姐。母亲,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请下者,我便收拾来也。(卜儿云)大姐,你在家执料,我去请那一辈儿老姊妹去来。(周舍诗云)数载间费尽精神,到今朝才许成亲。(外旦云)这都是天缘注定,(卜儿云)也还有不测风云。(同下)(外扮安秀实上,诗云)刘蕡下第千年恨,范丹守志一生贫。料得苍天如有意,断然不负读书人。小生姓安名秀实,洛阳人氏。自幼颇习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到此汴梁,有一歌者宋引章和小生作伴。当初他要嫁我来,如今却嫁了周舍。他有个八拜交的姐姐是赵盼儿,我去央他劝一劝,有何不可。赵大姐在家么?(正旦扮赵盼儿上,云)妾身赵盼儿是也。听的有人叫门,我开门看咱。(见科,云)我道是谁,原来是妹夫。你那里来?(安秀实云)我一径的来相烦你。当初姨姨要引章嫁我来,如今却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劝他一劝。(正旦云)当初这亲事不许你来?如今又要嫁别人,端的姻缘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妓女追陪,觅钱一世,临收计,怎做的百纵千随,知重咱风流媚。
【混江龙】我想这姻缘匹配,少一时一刻强难为。如何可意?怎的相知?怕不便脚搭着脑杓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后迟!寻前程,觅下梢,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料的来人心不问,天理难欺。
【油葫芦】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遮莫向狗溺处藏,遮莫向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
【天下乐】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
(云)妹夫,我可也待嫁个客人。有个比喻。(安秀实云)喻将何比?(正旦唱)
【那吒令】待妆个老实,学三从四德;争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端的是那里是三梢末尾?俺虽居在柳陌中、花街内,可是那件儿便宜?
【鹊踏枝】俺不是卖查梨,他可也逞刀锥;一个个败坏人伦,乔做胡为。(云)但来两三遭,问那厮要钱,他便道:"这弟子敲馒儿哩!"(唱)但见俺有些儿不伶俐,便说是女娘家要哄骗东西。
【寄生草】他每有人爱为娼妓,有人爱作次妻。干家的干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计。他正是"南头做了北头开,东行不见西行例"。
(云)妹夫,你且坐一坐,我去劝他。劝的省时,你休欢喜;劝不省时,休烦恼。(安秀实云)我不坐了,且回家去等信罢。大姐留心者!(下)(正旦做行科,见外旦云)妹子,你那里人情去?(外旦云)我不人情去,我待嫁人哩!(正旦云)我正来与你保亲。(外旦云)你保谁?(正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谁?(外旦云)我嫁周舍。(正旦云)你如今嫁人,莫不还早哩?(外旦云)有甚么早不早!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儿脓。我嫁了,做一个张郎家妇,李郎家妻,立个妇名,我做鬼也风流的。(正旦唱)
【村里迓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纪小哩,我与你慢慢的别寻个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铜斗儿家缘家计。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肠话劝妹妹,我怕你受不过男儿气息。
(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不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外旦云)你说我听咱。(正旦唱)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他终不解其意;那做子弟的,他影儿里会虚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实。(外旦云)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也堪爱哩。(正旦唱)那厮虽穿着几件虼螂皮,人伦事晓得甚的!
(云)妹子,你为甚么就要嫁他?(外旦云)则为他知重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他怎么知重你?(外旦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铺盖儿暖了,着你妹子歇息。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鐶。只为他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正旦云)你原来为这般呵。(唱)
【上马娇】我听的说就里,你原来为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冬月间着炭火煨,烘炙着绵衣。
【游四门】吃饭处,把匙头挑了筋共皮;出门去,提领系,整衣袂,戴插头面整梳篦。衜一味是虚脾,女娘每不省越着迷。
【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
【幺篇】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准?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云)妹子,久以后你受苦呵,休来告我。(外旦云)我便有那该死的罪,我也不来央告你。(周舍上,云)小的每,把这礼物摆的好看些。(正旦云)来的敢是周舍?那厮不言语便罢,他若但言,着他吃我几嘴好的。(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请姨姨吃些茶饭波。(正旦云)你请我?家里饿皮脸也,揭了锅儿底?窨子里秋月--不曾见这等食?(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门亲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谁?(周舍云)保宋引章。(正旦云)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儿?保他那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生儿长女?(周舍云)这歪刺骨好歹嘴也!我已成了事,不索央你。(正旦云)我去罢。(做出门科)(安秀实上,云)姨姨,劝的引章如何?(正旦云)不济事了也。(安秀实云)这等呵,我上朝求官应举去罢。(正旦云)你且休去,我有用你处哩。(安秀实云)依着姨姨说,我且在客店中安下,看你怎么发付我。(下)(正旦唱)
【赚煞】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缠郎君天魔祟。则他那裤儿里休猜做有腿,吐下鲜红血则当做苏木水。耳边休采那等闲食,那的是最容易、剜眼睛嫌的,则除是亲近着他便欢喜。(带云)着他疾省呵!(唱)哎,你个双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带云)一个夫人来到手儿里了。(唱)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下)
(周舍云)辞了母亲,着大姐上轿,回咱郑州去来。(诗云)才出娼家门,便作良家妇。(外旦诗云)只怕吃了良家亏,还想娼家做。(同下)
第二折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骑马一世,驴背上失了一脚。我为娶这妇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头,才成得事。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我骑了马,离了汴京,来到郑州。让他轿子在头里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话。则见那轿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抬轿的小厮,道:"你这等欺我!"举起鞭子就打。问他道:"你走便走,晃怎么?"那小厮道:"不干我事,奶奶在里边不知做甚么?"我揭起轿帘一看,则见他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来到家中,我说:"你套一床被我盖。"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那里?"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甚么?"他道:"我套绵子,把我翻在里头了。"我拿起棍来,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外旦云)我那里有这等事?(周舍云)我也说不得这许多。兀那贱人,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来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云)不信好人言,必有忄西惶事。当初赵家姐姐劝我不听,果然进的门来,打了我五十杀威棒。朝打暮骂,怕不死在他手里?我这隔壁有个王货郎,他如今去汴梁做买卖。我写一封书捎将去,着俺母亲和赵家姐姐来救我。若来迟了,我无那活的人也。天那,只被你打杀我也!(下)(卜儿哭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亲便是。有我女孩儿,从嫁了周舍,昨日王货邮寄信来,上写着道:"从到他家,进门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赵家姐姐来救我。"我拿着书,去与赵家姐姐说知,怎生救他去。引章孩儿,则被你痛杀我也!(下)(正旦上,云)自家赵盼儿。我想这门衣饭,几时是了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听的道谁揭债、谁买休。他每待强巴结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楼?一个个眼张狂。似漏了网的游鱼,一个个嘴卢都似跌了弹的斑鸠。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他每初时间有些实意,临老也没回头。
【逍遥乐】那一个不因循成就,那一个不顷刻前程,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和爷娘结下不厮见的冤仇,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儿机彀。他使那千般贞烈,万种恩情,到如今一笔都勾。
(卜儿上,云)这是他门首,我索过去。(做见科,云)大姐,烦恼杀我也。(正旦云)奶奶,你为甚么这般啼哭?(卜儿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听你劝,嫁了周舍,进门去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姐姐,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打了也!(唱)
【金菊香】想当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当初作念你的言词,今日都应口。则你那去时,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幸的班头,还说道有恩爱、结绸缪。
【醋葫芦】你铺排着鸳衾和凤帱,指望效天长共地久。蓦入门,知滋味,便合体。几番家眼睁睁打干净,待离了我这手。(带云)赵盼儿,(唱)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云)既然是这般呵,谁着你嫁他来?(卜儿云)大姐,周舍说誓来。(正唱)
【幺篇】那一个不嘇可可道横死亡?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则你这亚仙子母老实头。普天下爱女娘的子弟口,(带云)奶奶,不则周舍说慌也。(唱)那一个不指皇天各般说咒?恰似秋风过耳早休休。(卜儿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儿?(正旦云)奶奶,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卜儿云)他说来:"则有打死的,无有买休卖休的。"(正旦寻思科,做与卜耳语科,云)……则除是这般。(卜儿云)可是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将书来我看。(卜递书科,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奶奶:当初不信好人之言,果有忄西惶之事。进得他门,便打我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你来的早,还得见我;来得迟呵。不能勾见我面了。只此拜上。"妹子也,当初谁教你做这事来!(唱)
【幺篇】想当初有忧呵同共忧,有愁呵一处愁。他道是残生早晚丧荒丘,做了个游街野巷村务酒。你道是百年之后,(云)妹子也,你不道来:"这个也大姐,那个也大姐,出了一包脓!不如嫁个张郎妇、李郎妻,(唱)立一个妇名儿,做鬼也风流!"(云)奶奶,那寄书的人去了不曾?(卜儿云)还不曾去哩。(正旦云)我写一封书,寄与引章去。(做写科,唱)
【后庭花】我将这知心书亲自修,教他把天机休泄漏。传示与休莽戆收心的女,拜上你浑身疼的歹事头。(带云)引章,我怎的劝你来。(唱)你好没来由,遭他毒手,无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鲜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将性命丢!况家乡隔郑州,有谁人相睬瞅,空这般出尽丑。
(卜儿哭科,云)我那女孩儿那里打熬得过!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奶奶,放心!(唱)
【柳叶儿】则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个机谋。把这云鬟蝉鬓妆梳就,(带云)还再穿上些锦绣衣服。(唱)珊瑚钩、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儿别样娇柔。
【双雁儿】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割舍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个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说大口,怎出得我这烟月手!
(卜儿云)姐姐,到那里仔细着。(哭科,云)孩儿,则被你烦恼杀了我也!(正旦唱)
【浪里来煞】你收拾了心上忧,你展放了眉间皱,我直着"花叶不损觅归秋"。那厮爱女娘的心,见的便似驴共狗,卖弄他玲珑剔透。(云)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俱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撤了。我这里出了门儿,(唱)可不是一场风月,我着那汉一时休。(下)
第三折
(周舍同店小二上,诗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无非花共酒,恼乱我心肠。店小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我那里稀罕你那房钱养家?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头乱,一时间那里寻你去?(周舍云)你来粉房里寻我。(小二云)粉房里没有呵?(周舍云)赌房里来寻。(小二云)赌房里没有呵?(周舍云)牢房里来寻。(下)(丑扮小闲,挑笼上,诗云)钉靴雨伞为活计,偷寒送暖作营生。不是闲人闲不得,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自家张小闲的便是。平生做不的买卖,止是与歌者姐姐每叫些人,两头往来,传消寄信都是我。这里有个大姐赵盼儿,着我收拾两箱子衣服行李,往郑州去。都收拾停当了。请姐姐上马。(正旦上,云)小闲,我这等打扮,可冲动得那厮么?(小闲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么哩?(小闲云)休道冲动那厮,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则为他满怀愁,心间闷,做的个进退无门。那婆娘家一涌性,无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
【滚绣球】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输个姓因,怎不教那厮背槽抛粪!更做道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献勤,几番家待要不问;第一来我则是可怜见无主娘亲,第二来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到那里呵,也索费些精神。
(云)说话之间,早来到郑州地方了。小闲,接了马者,且在柳阴下歇一歇咱。(小闲云)我知道。(正旦云)小闲,咱闲口论闲话:这好人家好举止,恶人家恶家法。(小闲云)姐姐,你说我听。(正旦唱)
【倘秀才】县君的则是县君,妓人的则是妓人。怕不扭捏着身子蓦入他门;怎禁他使数的到支分,背地里暗忍。
【滚绣球】那好人家将粉扑儿浅淡匀,那里像咱干茨腊手抢着粉;好人家将那篦梳儿慢慢地铺鬓,那里像咱解了那襻胸带,下劾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个远近,觑个向顺,衜一味良人家风韵;那里像咱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个猢孙。有那千般不实乔躯老,有万种虚嚣歹议论,断不了风尘。
(小闲云)这里一个客店,姐姐好住下罢。(正旦云)叫店家来。(店小二见科)(正旦云)小二哥,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儿,放下行李。你与我请将周舍来,说我在这里久等多时也。(小二云)我知道。(做行叫科,云)小哥在那里?(周舍上,云)店小二,有甚么事?(小二云)店里有个好女子请你哩。(周舍云)咱和你就去来。(做见科,云)是好一个科子也。(正旦云)周舍,做来了也。(唱)
【幺篇】俺那妹子儿有见闻,可有福分,抬举的个丈夫俊上添俊,年纪儿恰正青春。(周舍云)我那里曾见你来?我在客伙里,你弹着一架筝,我不与了你个褐色绸缎儿?(正旦云)小的,你可见来?(小闲云)不曾见他有甚么褐色绸缎儿。(周舍云)哦,早起杭州客伙散了,赶到陕西客伙里吃酒,我不与了大姐一分饭来?(正旦云)小的每,你可见来?(小闲云)我不曾见。(正旦唱)你则是忒现新,忒忘昏,更做道你眼钝。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我为你断梦劳魂。(周舍云)我想起来了,你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你是赵盼儿,好,好!当初破亲也是你来!小二,关了店门,则打这小闲。(小闲云)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一房一卧来嫁你,你倒打我?(正旦云)周舍,你坐下,你听我说。你在南京时,人说你周舍名字,说的我耳满鼻满的,则是不曾见你。后得见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饭,只是思想着你。听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恼?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亲!(唱)
【倘秀才】我当初倚大呵妆儇主婚?怎知我嫉妒呵特故里破亲?你这厮外相儿通疏就里村!你今日结婚姻,咱就肯罢论。
(云)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奁房来寻你,你刬地将我打骂。小闲,拦回车儿,咱家去来!(周舍云)早知姐姐来嫁我,我怎肯打舅舅?(正旦云)你真个不知道?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门,只守着我坐下。(周舍云)休说一两日,就是一两年,您儿也坐的将去。(外旦上,云)周舍两三日不家去,我寻到这店门首。我试看咱,原来是赵盼儿和周舍坐哩!兀那老弟子不识羞,直赶到这里来!周舍,你再不要来家,等你来时,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递一刀子戳哩。(下)(周舍取棍科,云)我和你抢生吃哩!不是奶奶在这里,我打杀你!(正旦唱)
【脱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饶人,我为甚不敢明闻;肋底下插柴自忍,怎见你便打他一顿?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时节背地里使些村,对着我合思忖:那一个双同叔打杀俏红裙?
【幺篇】则见他恶哏哏,摸按着无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云)你拿着偌粗的棍棒,倘或打杀他呵,可怎了?(周舍云)丈夫打杀老婆,不该偿命。(正旦云)这等说,谁敢嫁你?(背唱)我假意儿瞒,虚科儿喷,着这厮有家难奔。妹子也。你试看咱风月救风尘。
(云)周舍,你好道儿!你这里坐着,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小闲,拦回车儿,咱回去来!(周舍云)好奶奶,请坐!我不知道他来;我若知道他来,我就该死。(正旦云)你真个不曾使他来?这妮子不贤惠,打一棒快球子。你舍的宋引章,我一发嫁你。(周舍云)我到家里就休了他。(背云)且慢着,那个妇人是我平日间打怕的,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休的造次,把这婆娘摇撼的实着。(向旦云)奶奶,您孩儿肚肠是驴马的见识,我今家去把媳妇休了呵,奶奶,你把肉吊窗儿放下来,可不嫁我,做的个尖担两头脱。奶奶,你说下个誓着。(正旦云)周舍,你真个要我赌咒?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的我赌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将酒来。(正旦云)休买酒,我车儿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还要买羊。(正旦云)休买羊,我车上有个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我买红去。(正旦云)休买红,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周舍,你争甚么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唱)
【二煞】则这紧的到头终是紧,亲的原来只是亲。凭着我花朵儿身躯、笋条几年纪,为这锦片儿前程,倒赔了几锭儿花银。拚着个十米九糠,问甚么两妇三妻,受了些万苦千辛。我着人头上气忍,不枉了一世做郎君。
【黄钟尾】你穷杀呵,甘心守分捱贫困;你富呵,休笑我饱暖生淫惹议论。您心中觑个意顺。但休了你这门内人,不要你钱财使半文。早是我走将来自上门。家业家私待你六亲,肥马轻裘待你一身,倒贴了奁房和你为眷姻。(云)我若还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都不晓得一些儿的。(唱)我将你写了的休书正了本。(同下)
第四折
(外旦上,云)这些时周舍敢待来也?(周舍上,见科)(外旦云)周舍,你要吃甚么茶饭?(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将纸笔来,写与你一纸休书,你快走!(外旦接休书不走科,云)我有甚么不是,你休了我?(周舍云)你还在这里?你快走!(外旦云)你真个休了我?你当初要我时怎么样说来?你这负心汉,害天灾的!你要去,我偏不去。(周舍推出门科)(外旦云)我出的这门来。周舍,你好痴也!赵盼儿姐姐,你好强也。我将着这休书,直至店中寻姐姐去来。(下)(周舍云)这贱人去了,我到店中娶那妇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恰才来的那妇人在那里?(小二云)你刚出门,他也上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儿了!将马来,我赶将他去。(小二云)马揣驹了。(周舍云)鞴骡子。(小二云)骡子漏蹄。(周舍云)这等,我步行赶将他去。(小二云)我也赶他去。(同下)(旦同外旦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勾出的这门也!(正旦云)走、走、走!(唱)
【双调】【新水令】笑吟吟案板似写着休书,则俺这脱空的故人何处?卖弄他能爱女、有权术,怎禁那得胜葫芦说到有九千句。
(云)引章,你将那休书来与我看咱。(外旦付休书)(正旦换科,云)引章,你再要嫁人时,全凭这一张纸是个照证,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赶上,喝云)贱人,那里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周舍,你与了我休书,赶出我来了。(周舍云)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外旦展看,周夺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碎我的休书也。(旦上救科)(周舍云)你也是我的老婆(正旦云)我怎么是你的老婆?(周舍云)你吃了我的酒来。(正旦云)我车上有十瓶好酒,怎么是你的,(周舍云)你可受我的羊来。(正旦云)我自有一只熟羊,怎么是你的?(周舍云)你受我的红定来。(正旦云)我自有大红罗,怎么是你的?(唱)
【乔牌儿】酒和羊,车上物;大红罗,自将去。你一心淫滥无是处,要将人白赖取。
(周舍云)你曾说过誓嫁我来。(正旦唱)
【庆东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
(云)引章妹子,你跟将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正旦唱)
【落梅风】则为你思虑,忒模糊。(周舍云)休书已毁了,你不跟我去待怎么?(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子休慌莫伯!咬碎的是假休书。(唱)我特故抄与你个休书
题目,我跟前见放着这亲模。(周舍夺科)(正旦唱)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周扯二旦科,云)明有王法,我和你告官去来。(同下)(外扮孤引张千上,诗云)声名德化九重闻,良夜家家不闭门。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小官郑州守李公弼是也。今日升起早衙,断理些公事。张千,喝撺箱。(张千云)理会的。(周舍同二旦、卜儿上)(周叫云)冤屈也!(孤云)告甚么事?(周舍云)大人可怜见,混赖我媳妇。(孤云)谁混赖你的媳妇?(周舍云)是赵盼儿设计混赖我媳妇宋引章。(孤云)那妇人怎么说?(正旦云)宋引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强占为妻,昨日又与了休书,怎么是小妇人混赖他的!(唱)
【雁儿落】这厮心狠毒,这厮家豪富,衜一味虚肚肠,不踏着实途路。
【得胜令】宋引章有亲夫,他强占作家属。淫乱心情歹,凶顽胆气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现放着体书,望恩官明鉴取。
(安秀实上,云)适才赵盼儿使人来说;"宋引章已有休书了,你快告官去,便好娶他。"这里是衙门首,不免高叫道:冤屈也!(孤云)衙门外谁闹?拿过来!(张千拿入科,云)告人当面。(孤云)你告谁来?(安秀实云)我安务实,聘下宋引章,被郑州周舍强夺为妻,乞大人做主咱!(孤云)谁是保亲?(安秀实云)是赵盼儿。(孤云)赵盼儿,你说宋引章原有丈夫,是谁?(正旦云)正是这安秀才。(唱)
【沽美酒】他幼年间便习儒,腹隐着九经书;又是俺共里同村一处居,接受了钗环财物,明是个良人妇。
(孤云)赵盼儿,我问你。这保亲的委是你么?(正旦云)是小妇人。(唱)
【太平令】现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怎当他抢亲的百计亏图?那里是明婚正娶,公然的伤风败俗!今日个诉与太府做主,可怜见断他夫妻完聚。(孤云)周舍,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你怎生还赖是你的妻子?若不看你父亲面上,送你有司问罪!您一行人,听我下断:周舍杖六十,与民一体当差。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赵盼儿等宁家住坐。(词云)只为老虔婆爱贿贪钱,赵盼儿细说根源。呆周舍不安本业,安秀才夫妇团圆。(众叩谢科)(正旦唱)
【收尾】对恩官一一说缘故,分剖开贪夫怨女。面糊盆再休说死生交,风月所重谐燕莺侣。
题目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正名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新梦青楼一操琴,是知音果爱知音。笺锦香寒,帕罗粉渗,遥受了些妆孤处
眼余眉甚。
【幺篇】腰瘦刚争不姓沈,被闲愁恼至如今。只为那镜约钗期,翻做了花毒
酒鸩,揣上一个罪名儿雨囚云禁。
【乔木查】狠姨夫计深,刀斧般恩情甚,蜡打枪头软厮禁。好姻缘苦用心,
他待独树成林。
【庆宣和】花有清香月有阴,一刻千金。辜负良霄可怜甚,问审,问审。
【落梅风】至如道烧银蜡,便做道度绣衾,托赖着这些福荫。三衙家则推道
娘未寝,不提防几场儿撒吞。
【风入松】耳边消息谩沉沉,情泪湿衣襟。强将别酒拼一任,奈新来酒也慵
斟。怕不待和愁强饮,却原来愁越难禁。
【拨不断】细思寻,厮淋侵,热温存漫想偎香枕。吉玎的生掂折玉簪,呆
答孩空忆酬红锦,要独强性儿急淋。
【离亭宴尾】口儿中不许别图个甚,意儿中既有何须恁?非瞒儿黑心,怎当
那冷撒吞柳青岑?错下书三婆啉,硬散楚的闲家谮。筝上弦怕支愣,井内瓶
愁扑井。这姻缘山高海深,倘若卦变了燕莺爻,交掷下鸳鸯兆,签抽的鸾凤谶。
牙缝儿唧与些甜,耳朵儿吹与些任。我则怕这锅水热不热今番在恁,你则待调弄
得话头儿长,承当的咒儿碜。
○题情
暗思金屋配合春娇,是那一点花星照也。向这欢娱中深埋了祸根苗,我一从
见了那个妖娆,他便和咱燕莺期,凤鸾交,鸳鸯侣,只引的蜂蝶儿闹也。恨不的
折损柔条,谁承望五陵人,可早先能够了小蛮腰。
【下山虎】向这芙蓉锦帐配合春娇,说不尽忄乞僧处有万般小巧。割舍了叶
损枝残,蕊开瓣凋,早一树烟华春事了。是咱思算少,又被傍人一觅里搅。猛可
里祆神庙顿然火烧,险把蓝桥水淹倒。
【山麻秸】计痛喋低低道,你休得为我愁烦,因我煎熬。多娇,犹兀自恐咱
憔悴潘安容貌。越着我气冲牛斗,恨填沧海,怒锁霞霄。
【恨薄情】为恩情,伤怀抱。追游宴赏情分少,朱颜镜里添老。书斋静悄,
不敢展文公家教。但只是磨香翰,挽兔毫,才下笔了便写出风情,翰林旧稿。
【四般宜】织锦字,寄英豪。焚金鼎,谢青霄。端详了云翰墨,越着我恨难
熬。全不写云期雨约,但只诉玉减香消。他道我风流性如竹摇,忄乞登的在咱心
上,默地拴牢。
【怨东君】他那里红妆残顿忘了楚娇,咱这里青衫湿渐成沈腰。他那里两泪
鲛绡,咱这里行里坐里五魂缥缈。耽烦受恼,是咱离多会少。莫不是普天下相
思病,我共他占了?
【江头送别】腌赞闷腌赞闷甚时断绝?恹煎病恹煎、病甚日医疗、又不
敢对着人明明道,只落的梦断魂劳。
【余音】眠思梦想如花貌,这愁烦谁人知道,守着这一盏残灯昏沉沉坐到晓。
暗思金屋配合春娇,是那一点花星照也。向这欢娱中深埋了祸根苗,我一从
见了那个妖娆,他便和咱燕莺期,凤鸾交,鸳鸯侣,只引的蜂蝶儿闹也。恨不的
折损柔条,谁承望五陵人,可早先能够了小蛮腰。
【下山虎】向这芙蓉锦帐配合春娇,说不尽忄乞僧处有万般小巧。割舍了叶
损枝残,蕊开瓣凋,早一树烟华春事了。是咱思算少,又被傍人一觅里搅。猛可
里祆神庙顿然火烧,险把蓝桥水淹倒。
【山麻秸】计痛喋低低道,你休得为我愁烦,因我煎熬。多娇,犹兀自恐咱
憔悴潘安容貌。越着我气冲牛斗,恨填沧海,怒锁霞霄。
【恨薄情】为恩情,伤怀抱。追游宴赏情分少,朱颜镜里添老。书斋静悄,
不敢展文公家教。但只是磨香翰,挽兔毫,才下笔了便写出风情,翰林旧稿。
【四般宜】织锦字,寄英豪。焚金鼎,谢青霄。端详了云翰墨,越着我恨难
熬。全不写云期雨约,但只诉玉减香消。他道我风流性如竹摇,忄乞登的在咱心
上,默地拴牢。
【怨东君】他那里红妆残顿忘了楚娇,咱这里青衫湿渐成沈腰。他那里两泪
鲛绡,咱这里行里坐里五魂缥缈。耽烦受恼,是咱离多会少。莫不是普天下相
思病,我共他占了?
【江头送别】腌赞闷腌赞闷甚时断绝?恹煎病恹煎、病甚日医疗、又不
敢对着人明明道,只落的梦断魂劳。
【余音】眠思梦想如花貌,这愁烦谁人知道,守着这一盏残灯昏沉沉坐到晓。
佳节喜逢长久日,魏文帝《与钟繇书》曰:“九月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惟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淳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翩翩凫_朋来。霜清天宇绝纤埃。老杜《九日》诗云:“天宇清霜净,公堂宿雾披。”遥怜巴岭月,严武有《九日巴岭答杜二见忆》诗云:“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拟上曲江台。老杜有《九日曲江》诗云:“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怀县从容留客宴,见老杜《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诗。追欢正好传杯。使君归骑莫相催。更拚明日醉,未放菊花开。
怀县从容留客宴,见老杜《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诗。追欢正好传杯。使君归骑莫相催。更拚明日醉,未放菊花开。
 陈普
陈普 王维
王维 关汉卿
关汉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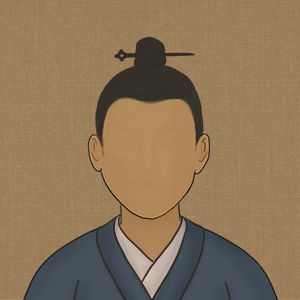 刘庭信
刘庭信 王元和
王元和 曹贞吉
曹贞吉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温庭筠
温庭筠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