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鉴赏
创作背景
猜您喜欢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日:“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壮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日:“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寓僧舍
秋色,秋色,几声悲怆,孤鸿出塞。满园林野火烘霞,荷枯柳败。
【踏莎行】水馆烟中,暮山云外,泊孤舟古渡侧。息风霾,净尘埃,宝刹清凉境界。僧相待,借眠何碍?
【垂丝钓】风清月白,有感心酸不耐。更触目凄凉,景物供将愁闷来。月被云埋,风鸣在籁。
【应天长】憎舍窄,蚊帐矮,独拥单衾,-宵如半载。旧恨新愁深似海。情缘在,人无奈,几般儿可怪。
【随煞】促织絮恼情怀,砧杵韵无聊赖。檐马奢殿铎鸣,疏雨滴西风煞,能断送楚台云,会禁持异乡客。
秋色,秋色,几声悲怆,孤鸿出塞。满园林野火烘霞,荷枯柳败。
【踏莎行】水馆烟中,暮山云外,泊孤舟古渡侧。息风霾,净尘埃,宝刹清凉境界。僧相待,借眠何碍?
【垂丝钓】风清月白,有感心酸不耐。更触目凄凉,景物供将愁闷来。月被云埋,风鸣在籁。
【应天长】憎舍窄,蚊帐矮,独拥单衾,-宵如半载。旧恨新愁深似海。情缘在,人无奈,几般儿可怪。
【随煞】促织絮恼情怀,砧杵韵无聊赖。檐马奢殿铎鸣,疏雨滴西风煞,能断送楚台云,会禁持异乡客。
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范云
范云 佚名
佚名 方苞
方苞 睢景臣
睢景臣 完颜亮
完颜亮 张孝祥
张孝祥 俞国宝
俞国宝 岳珂
岳珂 侯蒙
侯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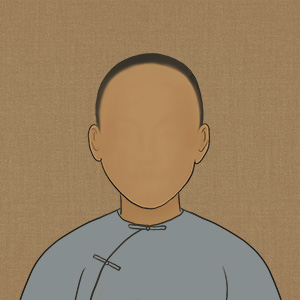 吴绮
吴绮 朱彝尊
朱彝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