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九嶷山上空白云飘飘,娥皇与女英乘着微风翩翩下山。
她们的眼泪洒在青青野竹上,片片红霞若天风织成绚丽的衣衫。
洞庭湖水波浩荡卷起白色的浪花,橘子洲当歌一曲感天动地。
我将为此而梦回祖国辽阔的河山,在芙蓉盛开的家乡朗照着清晨的光辉。
注释
帝子:指娥皇与女英。传说中,她们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
翠微:指青山。传说中九嶷山有娥皇峰与女英峰。
芙蓉国:指湖南省,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有“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长岛:今长沙的橘子洲。▲
创作背景
赏析
此诗起首二句毛泽东就以极其清新明朗的笔调,描绘出九疑山的明媚如画的景色,诗中用九嶷山点出了所描写的环境是湖南,并借用同湖南有关的神话,来描绘两位女神下山的情景,把读者带入一个优美而神奇的境界中。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笔下的这两位女神是“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楚辞·湘夫人》),充满了忧愁与悲凉;而毛泽东这里写她们是那样欢乐而明朗。巧妙地把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同新社会的美好现实作了鲜明的对比。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中,人民群众创造了无数奇迹,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把神仙也吸引来了。人间沸腾的生活,使天上的神仙都为之向往,毛主席挥动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彩笔,把神话与现实相结合,极为形象地从侧面描绘出大跃进高潮中祖国山河日新月异的变化。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二句紧接着写神女下山的形象。帝子乘风翩翩而来,由远及近,形象愈为鲜明。在往昔,多是“凡人”向往“仙境”,如今仙界神女竟然为“凡人”吸引而决意降临人间来了。实质上这里的“神女”与“凡人”是意味着不同性质的历史时代和深含着今昔对比之感慨的;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其从侧面意味深长地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自信:新时代终归比旧时代好。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两句写神女降临人间后的所见所闻。在“皇英二妃”的神话故事之后,毛泽东思及、写及“洞庭”“长岛”是颇自然的。神话故事中,二妃的神魂是游于洞庭湖南部与潇湘江边的,同时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1916年)就曾步行绕游“洞庭”一周,而“长岛”更是他青年时代与志同道合者“指点江山”之地,他从未忘怀过“洞庭”与“长岛”这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故乡名胜。“洞庭波涌连天雪”的气势磅礴的“意象”,充满着故乡人宏伟的精神气概;“长岛人歌动地诗”的“意象”,在称赞“友人”极具振奋力的诗作的同时,也可谓称赞了故乡人高昂的精神气概;颈联实质上是对故乡人当年所表现的精神气概的赞歌。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则是通过对湖南这一典型环境的描写,概括了整个中国的现实和历巨变,既表达了中国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自豪感,歌颂了光芒万丈的三面红旗,又展望了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还给人们指明了共产主义的灿烂前程,激励着人们坚定不移地向着共产主义迈进。并以朝阳的光辉乐观自信地展示对湖南故乡的美好愿望,同时希望“友人”对故乡湖南的光辉未来也要乐观地充满自信心。
全诗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以优美的神话故事作为诗的题材,前四句借“帝子”“斑竹”的故事和“红霞”的优美形象体现了湖南和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六两句是写现实,把人民群众干劲冲天、歌声动地的革命气势描绘得淋漓尽致。最后两句将现实和理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朝气蓬勃雄伟壮丽的大跃进图景,歌颂了人民群众在大跃进中的丰功伟绩和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并作为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简析
《七律·答友人》是一首七言律诗。该诗借友人赠诗赠物的话题展开联想,把神话、现实和理想融为一体,写出了故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表达了对友人的答谢,对乡情的思念,对乡人的祝福。同时也赞扬了人民的进取精神,预示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前程。全诗用笔巨细相补,取景大小映衬,写意虚实交错,诗风雄秀兼容,生动地体现了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一城秋雨豆花凉,闲倚平山望。不似年时鉴湖上,锦云香,采莲人语荷花荡。西风雁行,清溪渔唱,吹恨入沧浪。
赠琵琶妓王氏
舞腰回雪脸舒霞,席上人如画。压柳欺梅旧声价,弄琵琶.风流不似明妃嫁。金樽翠斝,玉纤罗帕,同醉凤城花。
忆疏斋学士郊行
飞梅和雪洒林梢,花落春颠倒。驴背敲诗暮寒峭,路迢迢,相逢不满疏翁笑。寒郊瘦岛,尘衣风帽,诗在灞陵桥。
春思
倚阑花影背东风,暗解清宵梦。舞扇歌衫与谁共?恨忡忡,一春愁压眉山重。灯花玉虫,罗屏金凤,残月小帘栊。
鉴湖夜泊
鉴湖一曲水云宽,鸳锦秋成段。醉舞花间影零乱,夜漫漫,小舟只向西林唤。仙山梦短,长天月满,玉女驾青鸾。
离情
几场秋雨老黄花,不管离人怕。一曲哀弦泪双下,放琵琶,挑灯羞看围屏画。声悲玉马,愁新罗帕,恨不到天涯。
山中
一方明月杏花坛,剑气霞光烂。回首蓬莱自长叹,佩秋兰,黄精已够山中饭。劳心又懒,干名不惯,归伴野云闲。
夜宴二首
砑金罗扇当花笺,醉草湘妃怨。曲曲阑干锦屏面,小壶天,花花按舞六幺遍。寒玉响泉,香风深院,明月十三弦。
翩翩白鹭伴诗癯,船系青山暮。一曲瑶筝写幽素,夜何如?飞吟亭上神仙路。琼楼玉宇,白云红树,月冷洞庭湖。
 毛泽东
毛泽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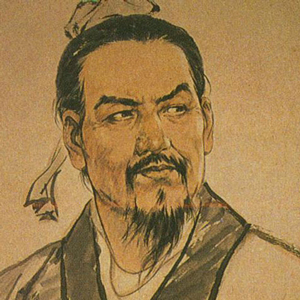 韩非
韩非 柳宗元
柳宗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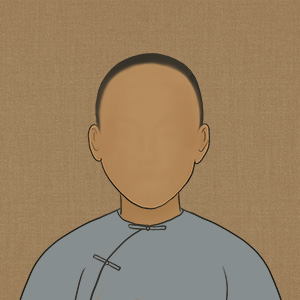 王举之
王举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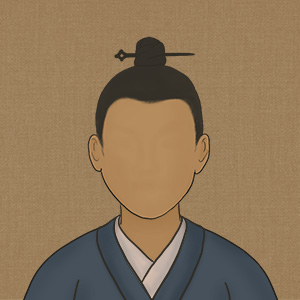 王元鼎
王元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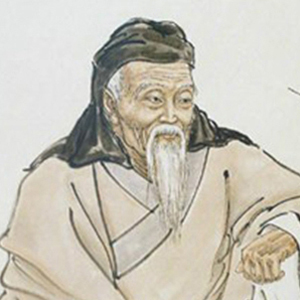 张可久
张可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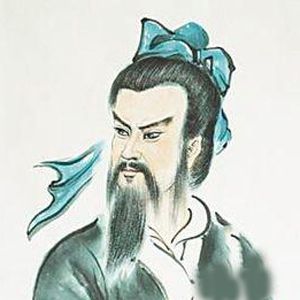 马致远
马致远 潘阆
潘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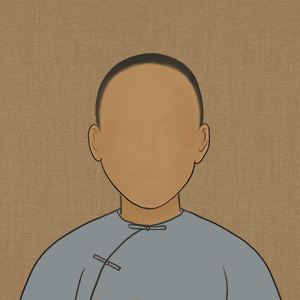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 赵长卿
赵长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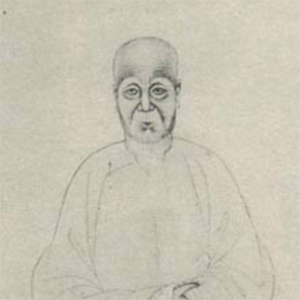 龚翔麟
龚翔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