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 曹侯浩然,人品高秀,玉立而冠,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因家乡别墅有萧闲堂,故自号萧闲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代文学家。宋宣和末从父守燕山,宋军败绩随父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完颜宗弼攻宋,与岳飞等交战时,蔡松年曾为宗弼“兼总军中六部事”,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卒谥“文简”。松年虽一生官运亨通,其作品在出处问题上却流露了颇为矛盾的思想感情。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民族意识使他感到“身宠神已辱”,作品风格隽爽清丽,词作尤负盛名,与吴激齐名,时称“吴蔡体”,有文集《明秀集》传世。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涂迍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蟠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
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无闻。
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晤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
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涂之愎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峣陉;建抚体以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回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冈岑纡以连属兮,溪谷夐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严壑以峥嵘。攒棫朴而杂榛楛兮,被浣濯而罗生。步亹菼与台菌兮,缘层崖而结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顾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
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汩以飙涌兮,气懆懆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
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
乘舫州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总伊瀍与涧濑。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操吴榜其万艘兮,充王府而纳最。济西溪而容与兮,息巩都而后逝。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害。
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 伫淹留以候霁兮,感忧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候风云之体势兮,天牢湍而无文。弥信宿而后阕兮,思逶迤以东运。见阳光之颢颢兮,怀少弭而有欣。
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挐其多远。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
乱曰:跋涉遐路,艰以阻兮。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咏江南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珠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爱杀江南!
咏遂闲堂
绰然亭后遂闲堂,更比仙家日月长。高情千古羲皇上,北窗风特地凉,客来时樽酒淋浪。花与竹无俗气,水和山有异香,委实会受用也云庄!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蔡松年
蔡松年 蔡邕
蔡邕 柳宗元
柳宗元 卢挚
卢挚 张养浩
张养浩 陈亮
陈亮 阎选
阎选 牛希济
牛希济 刘基
刘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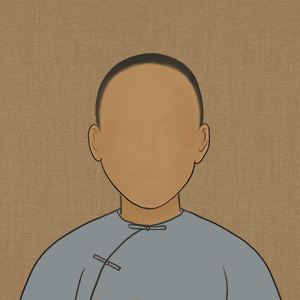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 王建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