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创作背景
赏析
王禹偁(chēng)(954—1001)北宋白体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汉族,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谪。真宗即位,召还,复知制诰。后贬知黄州,又迁蕲州病死。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学韩愈、柳宗元,诗崇杜甫、白居易,多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新平易。词仅存一首,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格调清新旷远。著有《小畜集》。
猜您喜欢
杜鹃啼过落花多,天气近清和。道人不管公家事,一樽酒抚掌而歌。吞海壮
怀寂寞,看山老眼摩挲。六龙飞去迅如梭,谁挽鲁阳戈?百年半逐云飞尽,青山
旧白发婆娑。但是石田茅屋,休言金谷铜驼。 寻春不遇
洞房香冷辟寒犀,花压翠帘低。弱红娇黛春无力,素鸾玉燕斜飞。鸳枕雨
云幽梦,鲛绡风月须题。一声啼画楼西,屈指又春归。等闲老却铅华粉,绿阴
满青子累累。莫问刘晨去远,可怜杜牧来迟。 钱塘即景
乱云如叶雨如丝,梅子乍青时。小□□□□余事,北窗下美酒盈卮。翠碗蔗
溶蜜汁,銮□藕□□□。□□当户碧参差,掩映万年枝。江南舶棹随风至,乌纱
润白苎滋滋。未拟兰舟避暑,且将纨扇题诗。 题货郎担儿
杏花天气日融融,香雾蔼帘栊。数声何处蛇皮鼓,琅琅过金水桥东。闺阁唤
回幽梦,街衢忙杀儿童 肚然一叟半龙钟,知是甚家风。担头无限□□物,希奇
样簇簇丛丛。不见木公久矣,可怜多少形容。
怀寂寞,看山老眼摩挲。六龙飞去迅如梭,谁挽鲁阳戈?百年半逐云飞尽,青山
旧白发婆娑。但是石田茅屋,休言金谷铜驼。 寻春不遇
洞房香冷辟寒犀,花压翠帘低。弱红娇黛春无力,素鸾玉燕斜飞。鸳枕雨
云幽梦,鲛绡风月须题。一声啼画楼西,屈指又春归。等闲老却铅华粉,绿阴
满青子累累。莫问刘晨去远,可怜杜牧来迟。 钱塘即景
乱云如叶雨如丝,梅子乍青时。小□□□□余事,北窗下美酒盈卮。翠碗蔗
溶蜜汁,銮□藕□□□。□□当户碧参差,掩映万年枝。江南舶棹随风至,乌纱
润白苎滋滋。未拟兰舟避暑,且将纨扇题诗。 题货郎担儿
杏花天气日融融,香雾蔼帘栊。数声何处蛇皮鼓,琅琅过金水桥东。闺阁唤
回幽梦,街衢忙杀儿童 肚然一叟半龙钟,知是甚家风。担头无限□□物,希奇
样簇簇丛丛。不见木公久矣,可怜多少形容。
湖上即事
断桥流水西林渡,暗香疏影梅花路。蹇驴破帽登山去,夕阳古寺题诗处。树头啼翠禽,水面飞白鹭,伤心和靖先生墓。
春情
疏星淡月秋千院,愁云恨雨芙蓉面。伤情燕足留红线,恼人鸾影闲团扇。兽炉沉水烟,翠沼残花片,一行写入相思传。
道情二首
直钩曾下严滩钩,清风自学苏门啸。蜜蜂飞绕管花帽,野猿坐守烧丹灶。扁舟范蠡高,五柳陶潜傲,南华梦里先惊觉。
雪毛马响狻猊革占,神光龙吼昆吾剑。冰坚夜半踰天堑,月寒晓起离村店。一身行路难,两鬓秋霜染,老来莫起功名念。
断桥流水西林渡,暗香疏影梅花路。蹇驴破帽登山去,夕阳古寺题诗处。树头啼翠禽,水面飞白鹭,伤心和靖先生墓。
春情
疏星淡月秋千院,愁云恨雨芙蓉面。伤情燕足留红线,恼人鸾影闲团扇。兽炉沉水烟,翠沼残花片,一行写入相思传。
道情二首
直钩曾下严滩钩,清风自学苏门啸。蜜蜂飞绕管花帽,野猿坐守烧丹灶。扁舟范蠡高,五柳陶潜傲,南华梦里先惊觉。
雪毛马响狻猊革占,神光龙吼昆吾剑。冰坚夜半踰天堑,月寒晓起离村店。一身行路难,两鬓秋霜染,老来莫起功名念。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残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残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王禹偁
王禹偁 刘致
刘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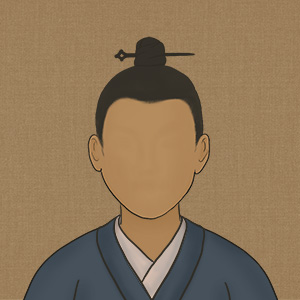 汤舜民
汤舜民 张可久
张可久 王琪
王琪 李珣
李珣 张元干
张元干 况周颐
况周颐 徐灿
徐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