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赏析
创作背景
[元](约公元一三二〇年前后在世)名、里、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其散曲《自况》云:“万倾烟霞归路,一川花草香车,利名场上我情疏。蓝田堪种玉,鲁海可操觚,东风供睡足。”可从中窥见其性情。散曲内容多写自然景物、离愁别恨或个人的闲适生活,风格清丽疏淡。阿里西瑛作嬾云窝成,自题殿前欢,西逸及贯云石等均有和作。西逸所作曲,今存小令四十余支。(见太平乐府)太和正音谱评为“如空谷流泉。”
猜您喜欢
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
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
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
路逢园绮笑向人,两君解来一何好。
闻道金陵龙虎盘,还同谢朓望长安。
千峰夹水向秋浦,五松名山当夏寒。
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陶公矍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
此中岂是久留处,便欲烧丹从列仙。
爱听松风且高卧,飕飕吹尽炎氛过。
登崖独立望九州,阳春欲奏谁相和?
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
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
肮脏不能就珪组,至今空扬高蹈名。
夫子工文绝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
吾非谢尚邀彦伯,异代风流各一时。
一时相逢乐在今,袖拂白云开素琴,弹为三峡流泉音。
从兹一别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
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
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
路逢园绮笑向人,两君解来一何好。
闻道金陵龙虎盘,还同谢朓望长安。
千峰夹水向秋浦,五松名山当夏寒。
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陶公矍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
此中岂是久留处,便欲烧丹从列仙。
爱听松风且高卧,飕飕吹尽炎氛过。
登崖独立望九州,阳春欲奏谁相和?
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
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
肮脏不能就珪组,至今空扬高蹈名。
夫子工文绝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
吾非谢尚邀彦伯,异代风流各一时。
一时相逢乐在今,袖拂白云开素琴,弹为三峡流泉音。
从兹一别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
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泪与秋河相似,点点注天东。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首已似飞蓬。年光愁病里,心绪别离中。
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见津亭。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
去去倦寻路程。江陵旧事,何曾再问杨琼。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
去去倦寻路程。江陵旧事,何曾再问杨琼。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杆处,正恁凝愁!(阑 一作:栏)
 吴西逸
吴西逸 李白
李白 白居易
白居易 谢灵运
谢灵运 张可久
张可久 马致远
马致远 蒋士铨
蒋士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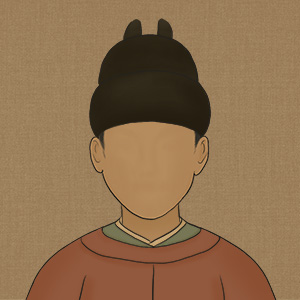 毛熙震
毛熙震 文廷式
文廷式 周邦彦
周邦彦 柳永
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