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坟诗
忠文峨眉英,始也迹甚微。堂堂薛简肃,旟隼西南飞。
其人古廉守,肯持蒟酱归。所得一伟人,天下大布衣。
引以宾王家,光映春官闱。昭陵宋仁主,前星久无辉。
犯讳言所难,雷电每霁威。雄哉鍊石手,妙补天巍巍。
丞相江南来,云掩扶桑晖。旧德陈苦辞,往往阨谤讥。
诸贤抗章疏,弱卒攻坚围。公力斡禹鼎,正气砰黄扉。
荆舒愤至骨,斥语笔自挥。赠之以蕙兰,何往无芳菲。
时公与司马,声谐玉琴徽。解冠挂神武,甘老西山薇。
九宇日瞀瞀,赤子将畴依。两公幸无恙,起拯或庶几。
嗣君元祐初,痛洗前人非。民望属司马,欲遁天为鞿。
帝命起公卧,门久车马騑。君实了吾事,此外何所希。
清风溢寰海,不啻严陵矶。公既晚家许,道德人所腓。
襄城下封竁,汝颍皆京圻。我来访遗垄,名姓存依稀。
来仍散兵烬,雨雪无留霏。公名在天下,岂逐薤露晞。
谁能禁耕牧,盛事乘薪机。吾力不足振,感叹徒歔欷。
(公元一二七九年至一三三八年)字子翚,号菊潭,先为隆安人,后徙顺阳。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卒于惠宗至元四年,年六十岁。勤于学。隐居不仕,学行为州里所敬。大德末,因荐授襄阳县教谕。文宗时,以书信拜见王约,王约看后对他的才能非常赞赏,就让他署任郡学正。此后又把他推荐到中书省,提升他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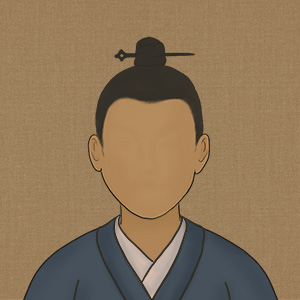 孛朮鲁翀
孛朮鲁翀 辛弃疾
辛弃疾 刘基
刘基 苏轼
苏轼 马致远
马致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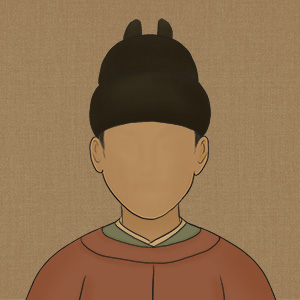 毛文锡
毛文锡 元好问
元好问 牛峤
牛峤 岳珂
岳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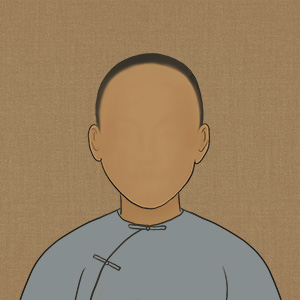 吴绮
吴绮 黄景仁
黄景仁